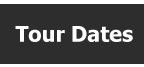|
以下張凱婷簡稱張。吳逸駿為吳
吳|最近在幹嘛?比如說最近三個月。
張|最近三個月,我在面對自己25歲之後體力跟腦力的下降。我覺得以前運用手指好像是一個很本能的事情,隨心所欲,但現在我的手開始有點不聽使喚。最近大象體操去美國表演,發現自己沒有辦法駕馭一個快速的16連音等等,所以我開始定期做復健。
至於內在的層面,我在面對一個很迷惘的階段。搬回高雄之後,我們決定以音樂作為志業,但是在作為志業之後,你會重新體會到必須要負擔的責任。這樣的責任是在大學階段,在台北開始玩這個樂團的時候從來沒有體會過的。例如說,我們就是彈出自己想要的音符,然後玩一些自認為有趣的對點,可能這一切都是其來有自,但並沒有想過那個其來有自到底是什麼,就直接去做。但是從開始以音樂作為志業之後,這些「我們的音樂從哪裡來?我們又要帶著這些音樂往哪裡去?」問題就浮現了,但它並沒有在一開始就浮現,這些事情讓我覺得非常害怕。
吳|是技術上跟音樂想法上的落差嗎?
張|對。
吳|身心靈無法統一嗎?
張|(笑) 有一點像是吧。就是想法開始轉變之後,會發現原來這件事情的深度跟廣度在這裡(高),而我們在這裡(低),然後現在要去把中間填補起來。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吳|為什麼可怕?
每天起來覺得自己沒有前進
張|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能力,然後在這個追逐的過程中我會不會失去原本創作這些音樂的動力,就是我覺得初衷有可能會消失......對我來說有一點像是一個無限空間,我每天起來都還是在同個地方。就是每天起來好像覺得自己沒有前進,被困在一個迴圈裡。
吳|可是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如果說我們沒有一個迴圈的話,我們會失去方向,因為你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張|可是迴圈一樣沒有方向。
吳|有阿。
張|可是他的方向會導回同一個地方。
吳|這樣可能就有前進阿。
張|我在期待前進,但我不確定這件事有沒有發生。
吳|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好,我覺得你超幸福的,因為你可以不斷回到同一個地方。可能我的理解不太對,但我覺得這樣很好。
張|所以你不會覺得這是被困住的?
吳|不是。因為你不管往哪裡出發都會回到原來的地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為這樣有目的也有方向。
張|但如果假設你真的把這件事情空間化了,他真的在一個地方;有點像是你重新回到這個點的時候,我好像沒有在餵養他,所以我重新回到這個空間的時候,草會有一點枯掉,然後再枯掉一點。
吳|這樣很好阿,四季就是這樣。
張|有可能耶,我現在有可能在經歷一個四季,然後在枯竭的那個時期。
吳|春夏秋冬阿這樣很好,妳有一天可能出門的時候發現要穿外套,但你回來的時候就已經熱了。我這樣聽起來還滿羨慕的,因為我現在沒有這種狀態,我現在狀態是直線的。
張|怎麼個直線法?
吳|就是一直走。
張|走去哪?
吳|不知道,問題就是出在這裡。比如說我每天出門上班、工作然後吃東西再回家,不是都一樣嗎?但這給人一個安定的感覺,做音樂最後和這些生活的事會疊在一起。你會發現你從這邊出發,到某個地方再到某個地方,最後還是會回來。最怕就是出去回不來。

害怕自己只是在模仿
張|我最近遇到一個新的問題,例如說我一開始喜歡陳綺貞,聽獨立樂團之後開始喜歡1976、Easy、橘娃娃等等;我覺得這些其實沒有影響到(創作)音樂本身,我創作的時候是很本能地在運用更早以前聽的東西,例如學木笛的時期一直在吹奏的巴洛克時期音樂。
可能我們的第一張EP、第一張專輯都有一點像是那樣的概念。後來我們因為大家的介紹,說「欸你們的音樂可能很像誰」例如American Football或者Toe,我們就開始去聽這些東西。但我在編曲的時候可能從來沒有想過Toe,這東西是後來的人給你加上的標籤。
我現在新的問題就是會想要開始模仿別人,我聽小山田圭吾,聽到各種器樂方面的編排,就會很深刻地開始想要利用這些音樂,我就覺得很可怕。現在在創作的時候,會想到小山田圭吾的編曲方法是很分開的,那是非常厲害的技法,他是一個頻率分配的天才。我就會覺得,天啊、好想做到這件事情,但就會變成模仿。
現在我們已經是一個以音樂為工作的團隊,當你有作品的時候,好像會有一個deadline有一個壓力要發表它;但我可能還在模仿的階段,我在重新模仿新認識的、那些很棒的音樂,但還沒有經過內化,我就已經要創作出新的東西,並且發表。我很害怕那種感覺,就我們被時間跟行程推著走。
吳|這我懂,可是問題是你會覺得這個很恐怖嗎?我覺得這好像還不錯,聽起來很帥,你每天都有很多新招,你的腦袋很活。這就像電風扇,它一直都在同一個地方轉,你會覺得它有生命力嗎?不會,它只是一個工具,但一隻蟑螂它就會到處跑,那就會有一個生命力。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未知的,音樂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所以才需要被創造,但如果我只是需要一點風,我就會拿電風扇吹。
但音樂不是這麼回事,沒有辦法像電風扇一樣,當你需要你就把它打開,不要的時候就關掉。所以我剛才聽一聽我還滿羨慕你的,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比如我覺得哪個音樂人很棒超屌的,我要跟他一樣;但後來發現我根本無法跟他一樣。像My Bloody Valentine的吉他手Kevin Shields,他說他從小就崇拜Jimi Hendrix,他卻發現他一輩子都沒有辦法變成那樣,所以他就玩他自己擅長,每一個吉他手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你喜歡什麼但你不會想要真正成為他,因為你想做自己,沒有人想要做台灣的小山田圭吾或者Jimi Hendrix的傳人。
張|我的確不想。
吳|到現在為止,你認為影響你最大的音樂或者樂手是誰。
張|這個影響最大是由我自己定義嗎?
吳|當然。

兩個影響,龜田誠治和坂本龍一
張|我第一個想到的絕對還是東京事變。(是龜田嗎還是整個團?)我覺得首先一定是龜田誠治,但是後來我會發現這個團的一切可能都像是我的一個夢,雖然我們在做的音樂跟東京事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我覺得東京事變給我很多啟發。
還有坂本龍一,雖然現在這樣講有點像在趕風潮。但是我在很久以前買了他的自傳,他在組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的時候,可能其他兩個人都是很流行音樂的路線,然後他是很古典樂的;但是各自提供idea的時候激盪出來的火花就很特別。
樂團有一點像是這樣,我們可能都有各自喜好的東西,各自提供出來之後創作。大象體操的東西一直都是各自的創作,沒有經過統整,對我來說東京事變的東西就很明顯有經過整合,但還是可以聽到各自突出的表現,我們離那個東西還很遠。
吳:貝斯手都很厲害,這個寫出來可能會被打,我認為Radiohead的貝斯手Colin Greenwood才是真正的音樂家,如果沒有那個貝斯其他的東西都是大便。
張|很常聽說如果沒有貝斯跟鼓這個團就不成立。
吳|對啊,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我在其他訪談看到,你製作音樂或錄音都在日本,也是因為東京事變的關係嗎?那到現在為止,你對日本的想像跟實際感受是什麼?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想像,第二個是實際的感受。
張|我原本的感覺是「空虛」。他們在很多的電影跟漫畫上都有這種感覺,就是「這不是現實」。他們為什麼文化創意產業可以那麼蓬勃,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在實現某種在生活中根本沒有辦法實現或沒有想要實現的虛幻的夢。
我去日本之後,這個想像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我覺得相對而言,台灣人是踏實的,不會懷抱著一個很奇怪的,對於生活或工作或環境可以塑造成怎樣的一個想像。
我喜歡看漫畫,例如請叫我英雄、彼岸島等等。他們也會在作品中實現災難,災難也是他們的某種夢,希望災難實現、而我是留下來的人,我是特別的。
吳|你去參與他們製作音樂的過程中,有感覺到什麼?
張|感受到的反而是音樂產業的面向。我非常欣賞日本音樂產業的一點是,他們的分眾很明確,並且在每一個不同的樂種或風格上,都會有唱片行或者媒體的支持,讓這件事得以繼續延續下去。日本有一間唱片行叫Stiff Slack Records,專門在經營比較器樂的東西。我覺得就像小白兔一樣,一間店或一本雜誌一個媒體的存在,當然還是會有一個波形會漲會跌,但日本在那個漲跌之間這些東西不會消失。如果是在台灣,他在跌的時候有可能會消失掉。
吳|那日本團對你的影響呢?
張|現在我覺得還好。
吳|即使你那麼喜歡東京事變?
張|對,我覺得那個感覺是欣賞他們的完整跟精緻,但是回到自己的話,我覺得創作這件事情還是要從內心出發,然後就會發現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那樣。

炫技的德布西
吳|古典音樂裡面你最喜歡誰?
張|我可以問你為什麼想問這個嗎?
吳|單純想知道,之前我看過一些訪問說你從小學古典音樂,所以我想知道,別人從來沒有問過這個,有也是帶過去而已。但我認為這蠻重要的。
張|我自己昨天有稍微想過,然後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是德布西。
吳|為什麼?
張|我在不同的階段都會重新喜歡上德布西。第一個階段是月光,因為我們家以前車上有這首歌,以前出遊的時候會開夜車,趁著禮拜五晚上開上高速公路,所以那個時候都很晚了。然後我們家車上的CD數十年如一日都是同一片。
吳|對對,大家都這樣子。
張|例如莫文蔚可能聽了十年,到現在還放在車上。我跟我哥那時候就是都會坐在後座,我們會順著椅背,讓自己的頭頂在那個可以看到窗外,就是車子那個後面那片玻璃,可以看到天上的夜空,那時候就在播月光這首歌,月光的低音部會有一個不間斷的六連音,我覺得那跟車子的運行真的太搭了,然後他同時又是一首溫和帶有月色的歌,我覺得月光對我來說就是公路旅行。
後來高中的時候,我記得我練了一首德布西的快樂島,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喜歡那種炫的東西。他在炫技上很有氣勢,我覺得每一個段落都是恰到好處。後來只要彈到結尾,主題大噴發的時候,我就會很激動,可能會哭之類的。
這首歌讓我感受到所謂才華跟炫技。為什麼他的音就是那麼特別,我就去問我媽「因為他用全音音階啊」,但我後來去彈那個音就很怪。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好好去運用全音音階寫出一個line。我覺得德布西讓他的每一首歌都有一點詭譎,就是因為這個元素被他fit in進去樂曲裡面,這是我很喜歡這首歌的原因。
吳|ok。
張|我覺得我會喜歡的東西分成兩種,第一種就是炫技派,例如音符的運行是很快速的、然後很流暢的,或是比較前衛的像是YMO好了,我就會覺得太帥啦。
吳|可是他們沒有很快欸。
張|YMO沒有很快,但是他們會有一些appregio(琶音)之類的。那個東西會讓你的心情被提起來。然後我喜歡的第二種音樂是很平緩的;我後來發現一件事,快速的旋律會讓很多的音都像是經過的,不會真正的留存,只是為了「構成」這段快速的音符而需要這些音。但是我覺得慢板的歌曲,每一個音都非常非常重要,可以感覺到每一個音的力道,但是在快歌裡我好像只能感受到整首歌的那個氣勢。
大概是這樣,還有我自己平常會去查來聽的,叫做「薩提Satie」Satie(Erik Satie)有首歌叫做Gymnopédies,那首歌就是我會單獨拿出來聽,就是像聽流行歌一樣,會夾雜在我的歌單裡。他就是很單純的配樂,每一個音都是很確實的存在,這是我現在會比較喜歡的古典樂。
手的困擾
吳|回到復健,你要推拿?
張|就是電療,醫生就說這是板機指的前兆。我好像有聽說你之前也需要復健那是怎麼了?
吳|等到你背樂器背到一個程度,例如十年好了。你一定會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樂器本身就不符合人體工學。
張|有沒有符合人體工學的做法?
吳|沒有,因為樂器是符合音律,不是為了符合人體工學而被創造的。吉他貝斯,或是鼓都不符合人體工學,他左右腳的分配比重不一樣,慣用腳慣用手這些,都會有運動傷害的問題。我遇過太多運動傷害的鼓手,打五年就出問題了,尤其是Metal。我認為這種事情就就是一個累積性的東西然後突然「啪」!發生了。
張|因為我爸是牙醫,所以像他現在也是有職業傷害。
吳|做一些精密的事情就很容易這樣,像我之前錄音用到很多小肌肉,需要做很細緻的動作,久了我就整隻手都廢掉,連pick都拿不起來會掉地上。
張|那怎麼辦?
吳|我就一直復健啊,我經常表演到一半pick掉地上,就再把pick撿起來或者不用pick,我以前上台要吃止痛藥。
張|可是你很快就接受了這件事嗎?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巨大的......
吳|我很快就接受了,因為人不會不受傷。
張|但你那時候知道你會康復嗎?
吳|不知道,只能這樣啊,不然怎麼辦?把手砍掉?我以前還有五十肩,連攔計程車都沒辦法。
張|我現在有點覺得自己是小巫見大巫,我只是有時候沒辦法控制而已。我覺得身體會一直提醒你,就像我現在還是可以直接地感受到那個痛楚是一直在發生的。
吳|像我以前刷很快,我現在刷超慢的,為什麼,因為這些事情會逼迫你去適應。而我認為身體的狀態也是一種音樂性,當你無法彈到180的時候,你只要彈120就好,你把120做好聽,並不會妨礙到你。
張|可是心態上你不會覺得這是一種妥協嗎?
吳|不會,這完全不妥協,我還是在做音樂,我不會因為我彈不到180我就放棄音樂,你不會因為你現在手傷就放棄音樂嘛對不對,這本身跟放棄沒有關係,你就是帶著他(傷)就好了,我覺得帶著他就跟你揹著一把貝斯一樣,是你身體的一部分。

在音樂上的拆解和重組
吳|做音樂時你在想什麼?
張|我喜歡先照本能來彈奏,例如說沒有貝斯的音樂,或是我自己找出一段鼓的riff,然後我先靠本能去彈出我自己覺得很棒的旋律,因為現在電腦很方便,我會在logic裡面把每一個音拆開。也就是說我明明已經彈出一個完整的東西了,但是我會把他拆開之後,用有一點隨機的方法重新組合。
吳|一直重組嗎?
張|對,重新亂剪,而且那亂剪真的就是無意識的去做這件事情。並不是說「欸我記得我這時候彈這個音,所以我想要把他抓過來」,我需要那個刺激,需要去從自己原生的創作裡,找出一個新的可以刺激我聽覺的line。我在創作的時候,會想要從自己的身上,找到原本沒辦法做出來的東西。
吳|沒有辦法做出來的事情?
張|就是靠我自己的本能沒辦法想到的那段音樂。
吳|你想要做那個,原本沒有想到的事情?
張|對,那些音是我原本可以想出來的,但是這個排列組合是一個全新的東西。我玩音樂的時候就是會很喜歡玩這個。
吳|拆解、組合。
張|其實我自己寫的歌裡面,有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就是我原本彈不起來,但是我用電腦軟體去把它剪起來之後,我可以彈起來,然後他又再度成為我的東西。
吳|這樣很好啊。
張|我覺得就是玩遊戲,你問我,我創作音樂在想什麼,因為我覺得我創作一開始就是在玩遊戲,我不想要放棄這些東西。
吳|那你的精神狀態是什麼?
張|我的精神狀態?
吳|因為你玩遊戲是你的目的。
張|我的目的?我覺得算是一種動機吧?就是可以玩這件事,促使我想要去創作。
可以「玩音樂」,促使我想要去創作
吳|ok,那比如說我不讓妳想彈的東西,我是你老闆,你要照這樣彈。
張|那我可能就沒那種動力了。
吳|但是有給你錢,錢算不算動力?
張|錢算不算動力喔?不太算吧!
吳|所以妳現在是,不能用錢買的就對了?
張|基本上是。因為我的物質慾望有點低。
吳|等妳需要十把貝斯的時候,或是換一台好一點的電腦?
張|我們樂團現在有給付,就是每個月的基本薪資。
吳|樂團誰付錢?
張|凱翔付。
吳|他為什麼可以付?
張|為什麼可以付?就是我們會算一年如果每個人要拿最低基本薪資的話,我們應該要賺多少錢,然後我們就依照這樣的量去接表演。
吳|喔所以說是賺來的!
張|對啊,是要賺來的,靠樂團賺來的。
吳|下一個問題,你在網路上自拍彈bass有帶給你什麼嗎?
張|我想要先問你為什麼想問這個問題?
吳|因為我一直看到,而且從來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張|應該說這個問題乍聽之下會覺得非常尖銳,我也會相對想說你想要得到什麼答案?
吳|我沒有預設答案。
張|真的嗎?
吳|我沒有預設答案啊,任何問題我都沒有任何預設答案。

彈貝斯自拍上傳,讓所有人都變成我的老師
張|我覺得這跟我學習的歷程很有關係。我高中的時候曾經跟一個在高雄的老師學琴。那時候在Att。然後也有在舞廳演奏。他教的東西非常基礎,在我最害怕基礎的高中時期,對我而言十分枯燥乏味。
到了大學我跟方Q(宇宙人)上課,老師上課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架構。台灣大部分搖滾樂老師不像古典樂有一個學習的進程,每個老師都是照著自己認為你需要學什麼就給你什麼。那時候跟方Q上課,他會說那你今天就來學這個;接著就會彈一整段solo,我可能要坐在那邊聽15分鐘、或是20分鐘,然後叫我練起來。
這個是我們上課的方式。那時候他叫我練什麼,我就練什麼,但是也沒有從基礎開始打起,是比較隨性的,但我覺得很有趣,像他叫我練嗆辣紅椒,我就練。
我開始做自拍影片是去日本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在小套房裡面生活。我去買了一把琴,日本的一個小廠牌history。那時候正在休團,我覺得應該是開始重新學習一些東西的階段;就回去問方Q、或是身邊的朋友,我要怎麼樣去好好的、紮實的練習。
然後他就說可以拍影片上傳,等於我是被建議的啦。
吳|方Q建議的喔?
張|方Q還有體熊專科的吉他手包子。我在過程中也體會到,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有幫助,就是受到關注這件事會督促自己,這是一個我覺得很直接的心理狀態。
例如我以前學鋼琴的時候,老師就是關注你的人,那個角色會讓你很緊張,我覺得上傳影片的時候,所有人可能就會變成我的老師。
因為我自己待在那個公寓裡面,如果單純做這件事情我沒有辦法受到這樣的關注,而我覺得(上傳)網路平台會督促我做這件事情。然後我覺得最棒的就是,我身邊的人會批評我。像金魁剛,Trash的鼓手,他同時貝斯也彈得很不錯,會願意跟我討論;例如說我在練D’angelo的歌,他會說你的長短音根本不對,他們會告訴我沒有注意到哪些事情。
就像練習古典樂一樣,他在樂譜上會有例如說Andante 、然後這裡慢等等的,那東西很明確。
但是當你在cover一首歌的時候,沒有人會告訴你這些東西,要用感受的。cover歌最初期真的就只是想要把他彈出來,到後期才是真的喜歡這段貝斯,可能就是喜歡他那個groove的點,所以就應該要真的去找到並且彈出那個點,才會實現練習的目的。
如果當初沒有把這些東西放在平台上,就不會得到這些意見,也不會讓我進一步體認到我為什麼會去喜歡一段貝斯。以前的喜歡可能就只是喜歡,現在就是可以去找出有哪些元素這樣子。但我沒有買廣告啦。
但這件事情有一個後續的效應就是,大家會開始覺得這可能是一種手段,就會有人想要讓你幫他們曝光,這是一個後續的效應。
吳|幫誰啊?可以講一下嗎?是商業嗎?
張|就是找我cover別團的歌,但我覺得沒有到商業的程度。
吳|那你幫co一下我們團的歌哈哈。
張|我覺得我那段時間練琴練得還不錯。而且那是一種挑戰,因為錄影片的時候不能中斷。如果我只是私底下cover一首歌,我可能就是一段一段練,也不會一定要從頭到尾彈完它。
最討厭的是自己,討厭自已比討厭別人大三倍!
吳|最後一題,你有討厭的人嗎?
張|我想問你為什麼想問這個?哈哈哈這是通常訪問都會問的問題嗎?
吳|不是通常都會問的。你有討厭很多人嗎?可以不用講人名。
張|你問到說我有沒有討厭的人的時候,我有兩三個名字跑出來。但是我覺得今年是反省之年。我覺得射出去的箭到最後都是回到自己身上,假設我對這三個人好了,討厭的程度全部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我現在有三倍的討厭。
吳|所以妳現在最討厭自己?
張|現在最討厭自己。對。因為我覺得討厭別人這件事情......
吳|負面能量。
張|如果是很坦率地面對自己的負面能量,並且很誠實地去討厭一個人,我覺得沒關係。但是我發現沒有所謂純粹的討厭,就是討厭裡面絕對包含著自己的有限。
吳|例如說嫉妒。
張|對嫉妒,或者是你覺得他很像自己。就是當你已經不是很純粹地在討厭一個人的時候,那東西是不坦率的,所以最後還是會回到自己身上。
吳|ok不錯欸,我覺得很讚,我覺得你講得很好。我覺得你今天這part講最好。
張|對不起
吳|幹嘛對不起?
張|沒有,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在整個進程中我會變得越來越沈淪、越來越不會回答問題,然後對自己的答案沒有把握。
吳|不會,我覺得這種事情就是這樣,就是一種互動。妳、我每一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一面,而每一個人都會想要保留不為人知的一面。但是對訪問者來講,卻面臨這個壓力。就是說他也許想要知道你內心的秘密,但是他也不是那麼想知道,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張|所以這就是一種互動?
吳|所以有些問題很尖銳的意思,並不是真正尖銳,你如果說有人問過更尖銳的,我就不會問這些,因為那就是涉及隱私、或是涉及八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