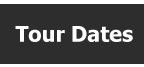|
以下許正泰簡稱許,吳逸駿簡稱吳,葉宛青為葉
吳|之前有看過一些其他媒體的訪問,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讓我有一種感覺是「你會很著急」;比如說A做完了,停一下B又要開始,對你來說是一個常態嗎?
許|過去我覺得是一個常態,因為我確實是很著急,很想要趕快做一些事或者出專輯趕快錄音。再加上我覺得我們年紀都已經到了不是那麼瀟灑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生活上的焦慮。
而且我也沒有存款,也沒有事業,那時候當然會想要做很多嘗試,所以一直換團員一直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常常基本的事情沒有做好,像是歌沒有做完就想要表演或者錄音,錄下來又不滿意,就會很挫敗。
吳|你的團或團名換了很多啊?
許|那時候是因為傷心欲絕決定不要玩了,我跑去跟除了劉暐之外的人組了另外一個團,可是那個團幾乎沒有活動;我們只表演過一場,可是做了很多歌。那兩年我大概三十歲,基本上就是在尋找一個能夠讓生活穩定一點的狀態,所以那個時候做音樂,我都不敢聽以前的專輯。
那個時候會一直想要做出新的東西,會覺得以前做音樂的想法太隨便了,沒有耐心去面對音樂內容,所以那兩年就是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研究,那後來生活也習慣了新的狀態,那個不一樣是例如酒喝得比較少,比較會開始想說我做音樂這件事到底是什麼意義,到最後雖然沒有找到什麼意義,至少習慣了一種焦慮的狀態,也比較可以坦然一點。
以前對音樂超不負責任的
吳|就是直接幹下去?
許|對,我20歲到25、6歲完全沒有在想這些事。那個時候把自己的一些懶散都歸給龐克,覺得這樣比較率性,以前真的不會想那麼多。我這幾天才在跟團員說「哇我以前對音樂超不負責任的」。
葉|你說你那時候的焦慮是因為快要三十歲,那現在有什麼改變?
許|我不覺得有改變,生活的焦慮還是很嚴重,現在就是知道做什麼事會讓自己平靜一點。對阿所以我現在覺得很煩,但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所以都還是會傻傻地照著之前的模式走。其實我都不敢看我自己的表演,因為那個狀態是在我自己生活中找不到的。
吳|你現在有漸漸解決這件事嗎?
許|我覺得有進步但是沒有解決,最主要的焦慮來自於我沒有任何成就,我也沒有留下甚麼可以被說的事情,而且我那麼窮。
草東和落日他們幹得不錯
吳|所以這個焦慮是物質上的?可是我覺得indie團多少都會有這個問題啊。像我30幾歲時候會覺得睡太多了,但是現在我覺得睡太少了...。
許|我覺得我現在在物質上沒有辦法滿足的話,心靈也沒有辦法滿足,就算我做出一首很好聽的歌,他其實不會為我帶來什麼,總是覺得就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的話,那好像他帶給我的安慰是沒有依據的。
樂團本身是不可能給你帶來什麼物質上的保障,那因為我們年紀都差不多大,當然會覺得草東沒有派對或是落日飛車他們幹得還不錯,就變成自己的焦慮。
吳|比如說你辦一場演出,那這樣一晚上滿場收入通常應該有兩萬塊以上...我亂猜,然後可能一個月一次。
許|我們沒辦法每次都滿場。
吳|現在演出的頻率大概是多久一次?
許|上次是發片然後二月也有再辦一次專場都有滿,但我們有六個人,而且這個團平常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收入。
做音樂的成就感?
吳|最新的這張專輯離上一張五年,為什麼會隔這麼久?
許|中間就一直在換團員阿散團。
吳|你覺得這樣好嗎?
許|當然不好啊,現在也不會像以前那樣處理樂團的事情,那個時候確實就是很焦躁生氣...。這中間當然發生了很多爛事,包括散團,主要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要玩樂團,也沒有為我帶來什麼事業或錢,他也沒有變成一個不錯的團,還是一個爛團。
吳|可是你不覺得做音樂本身如果沒有基本的成就感的話,也很難繼續,對你來說有嗎?在新專輯出的時候?
許|有一點點但是現在也沒有了。
吳|所以創作的過程或是錄音的過程也沒有成就感?

創作的過程中沒有成就感
許|沒有。
吳|那你怎麼有動力做音樂?
許|我在錄音的時候以為錄出來會很喜歡,就促使我去做這件事。可是出完之後,有一陣子我還滿喜歡的,大概兩個月吧。過後就不喜歡了,我覺得自己的音樂技巧很差,不管是編曲、唱歌,跟其他人比都不是同一個水準。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現在還繼續做這件事,我只是覺得做音樂還是很好玩,還有太多事情值得去研究。最主要是像我們以前,前面的人就只有五月天,離我們太遠,那我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後我們可以不用做其他事情。現在草東跟飛車出來後,至少是離我們比較近的目標,而且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模式。我覺得我們缺這樣子的典範,在我長大過程中完全沒有,所以我會玩得很掙扎。我覺得現在的團比較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他要賺錢的話有哪些步驟,這個模式出來很重要。
吳|我在想做音樂這件事,我十年前看獨立音樂場景的時候會覺得沒有集體感,比如我是傷心欲絕的歌迷,我去看演出我就知道要做什麼,可是以前比較沒有;可是我看現在比如草東的樂迷,他很清楚他今天來要幹嘛。你有這個感覺嗎?你會怎麼看待這個差別?
許|當然有阿,大家比較知道怎麼宣傳自己,知道怎麼讓樂迷知道自己在幹嘛,現在傳播太容易,大家手法都很高明。
吳|你覺得是網路宣傳的關係嗎?
許|首先我覺得現在的樂團比較知道怎麼把來看表演當作是一種娛樂來宣傳,所以樂迷來就會知道可以期待什麼,再來是,現在樂團知道是一種娛樂了,所以他們(樂團)講的很多理念也是為了塑造他們娛樂的面貌。就像你去看恐怖片,他的宣傳就會讓你知道你去是要被嚇。
吳|就像是我今天如果去濁水溪公社的場子就會知道要幹嘛...。
許|而且現在的樂迷數量也比以前成長很多,就有基礎可以做這樣的事情,以前你可能怎麼宣傳也很難盛況空前。
吳|所以其實,按照這個做法,你剛剛講的是說,在台灣的樂迷基本盤有變多。
許|我覺得現在團的旋律真的太厲害了,他們是真的很好聽,雖然說我都會很嫉妒,但真的是很好聽。
吳|你是說草東嗎?(笑)真的這麼好聽?
許|我覺得啦。
吳|其實我聽草東也是大概前兩年,是真的不錯。但是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差別是,樂團跟樂迷之間互動的模式,跟以前不太一樣。
許|可是你覺得,專屬於某個團的樂迷,這是好事嗎?
吳|我覺得草東就是這樣子呀!我覺得他們不聽別的音樂欸。
許|喔可是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過程,他把這些人帶來音樂領域的,算是領路人吧。
吳|就跟五迷一樣,我認為五迷是不聽別的音樂的,不然他們怎麼有辦法這樣子、一直聚焦在同一個東西上,比如說他們唱十場,我就買十場。這樣他們怎麼有空聽別的音樂,你理解我的意思嗎?他們已經塞滿了五月天。
許|裡面也至少有一半是會喜歡、也會喜歡其他音樂的。
吳|真的有嗎?
許|我覺得這個文化是不一樣的,一種是groupie文化,台灣本來比較缺少groupie文化。現在這個文化開始有了,groupie就是你怎樣我都買單;這東西漸漸有之後,才有可能再去延伸到更廣大的群眾。
吳|嗯你這觀察蠻有道理的。

我看得懂的就是字,所以我做熱鬧一點的雜誌
吳|你做雜誌,做那些zine是為了什麼?就是說,也是想要填滿你其他,沒有辦法花掉的時間?
許|我覺得台灣的地下出版太荒了。我自己其實還是喜歡看字的,像我去看地下市集、裡面很多photo zine;但我其實是對影像很遲鈍的人,所以我看不太懂,我看得懂的就是字,寫得夠清楚。我平常有在寫東西,那我想也不會有人幫我出版,所以就自己出,然後我自己出的話,當然會找旁邊的朋友,他們在搞什麼就一起把它放進來,做個熱鬧一點的雜誌。
吳|經費什麼的呢,自己找?
許|就自己出啊,要自費出一本,其實不貴啦。自己出的唯一個缺點就是沒有辦法一直出,因為賣書需要一段時間,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出了三期,至少都回本。
吳|真的喔?你們賣幾本?
許|第一本是,我辦一個活動叫樓下聯誼,然後我們印了450本賣完了,其實大概100本就回本。
吳|100本就回本,那你賣了450本,也算是賺錢。你怎麼去接觸到你的讀者?
許|其實我也不知道,一開始是在我們活動那天賣,就賣了大概80本,之後就是到處聯絡書店,就那種獨立書店,然後讓他們進貨、寄賣。
吳|應該是說,那種微型的狀態,會比較容易達到。
許|現在就只能做微型的,內容沒有辦法做得很正式,我也沒有能力去編一本正式的東西。
吳|那你會繼續出嗎?這zine。
許|會。
吳|那你挑選的標準或方向是什麼?
許|沒有一個很嚴肅很正經的方向,基本上就是我現在有作品、旁邊的朋友有作品的話,我就會把他拿來出,看有什麼就可以出。
吳|這跟做音樂很不一樣對不對?音樂你要編曲、會花很多心力什麼的。
許|因為我對音樂還是比較有感覺,對音樂會有比較嚴謹的編排以及品質的要求。可是做zine基本上就是把我自己覺得好玩、但不是真的那麼好的作品讓別人看到。不一定要準備得非常完全才會出版,所以是比較chill的一件事。
吳|那你會繼續做音樂嗎?
許|會啊。
吳|做音樂這件事就我個人經驗,我其實很少去想到商業模式;但是賣錢是基本的,就是要推到市場上去賣,然後到底能不能賣,很難有一個模式。因為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商業模式可言。
許|其實這一年商業模式出來了,基本上他就是找到一個除了台灣以外的地方,然後可以有一個更大的市場。
吳|那假設,台灣的樂團如果都往中國、或是東南亞跑,那真的有局嗎?比如說我現在簽下傷心欲絕,然後幫你們排中國巡迴,你覺得會通嗎?
許|他會work啊。
吳|事實上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應該要有,這件事情應不應該發生?對你們來講。
許|沒有。
吳|你們會不會期待這件事情發生?
許|還好。
吳|為什麼?你不是說商業對你們來講很重要?
吳|國外的agent對我來說都還好,因為現在不一定要有agent,你才能去國外表演。現在你只要在當地有一些認識的人牽線、場地排好就可以去表演;可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當地的宣傳,就會沒辦法做。
許|欸對,為什麼你沒有問我關於龐克的一些事情?
吳|我一開始就要問你啊。
許|因為最近的訪問一定都會講到龐克。

龐克太囉嗦了,現在不在我的生活中
吳|我的問法比較直,不是音樂;而是龐克這件事情。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嗎?
許|他現在已經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這樣的事當然是讓我變成現在的我的樣子的原因,但龐克也是人家規範出來的一個典範,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定要變成的狀態。而且龐克現在變得很教條,所以我也不覺得我是龐克,或是龐克對我來講有什麼重要的。
吳|你會想到,你要玩龐克這件事嗎?
許|不會,完全不會。
吳|那你們做最新這張專輯,你會想這件事嗎?可是你又說龐克形塑了你,然後你現在又毀滅他,然後說你已經解脫了?
許|他不再重要了,龐不龐克對我來說已經沒什麼差。而且我覺得龐克現在已經變成好像信仰、或是宗教的東西。一種東西一但變成宗教,他就會變成很多你想不到的.....。
他太囉唆了,想說的東西一但變教條,就很囉唆,而且他太簡單,太簡單去劃分一群人。
吳|在那個當下,是不是大家都覺得,我可以。
許|當然啊,比如你要說你是一個龐克,你要先相信、先有這個信仰。可是我覺得要我現在說我是龐克,那就很不誠實啊,因為他也沒有實現在我的生活當中。
吳|所以說龐克現在不是你的生活、也不是你的信仰就是了。
許|他不是啊,他不是我的信仰,如果你說你是龐克,你做所有事情都有一個原因,有一個概念,好像你不是只為你自己服務,好像是為一個更高的東西服務,可是我沒有。
吳|其實我前面有問到這個,只是確立幾個標題,這樣我覺得不錯,你覺得你還有什麼想要講的嗎?
許|沒有。
吳|好。
關於其他更重要的問題:
葉|你長得這麼高,在台灣要怎麼買褲子?
許|這也不是什麼問題,因為我也不穿夠長的褲子啊?我從來不知道合適的褲子長度是到哪裡,該到腳踝還是鞋子?UNIQLO的34腰長度大概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樣,我還可以摺起來,大概碰到鞋舌……褲子長度有很重要嗎?我不知道怎樣叫作合適的長度??
葉|你是先寫字再做音樂嗎?
許|不是,我本來是SPUNKA的鼓手,很白痴的樂團,很年輕又很幼稚。後來我開始自己寫歌,一方面也是覺得自己不是特別有天份,於是對打鼓失去熱情,很疲乏,另一方面我也找不到團員,就不再當鼓手,改彈吉他唱自己的歌。我喜歡Nirvana、Green Day、Blink 182還有Ramones的鼓手。會覺得他們很厲害,想要變得跟他們一樣,但後來仔細想想,我其實沒有很正經地思考過鼓手這個職位,打鼓一開始對我來說就不是這麼正經的事情,當初打到可以配歌就組團了。
葉|你讓自己有很大的餘裕可以感受世界,這樣的狀態是你刻意維持的嗎?
許|我小時候牌氣很壞,覺得不是很多人喜歡我,我在人際關係上不是很得體或得手,所以我青少年時期一直很刻意要讓自己變成得體的人,一個較為全觀的人。在任何場面盡量讓自己很公平,有魅力地解決朋友之間的矛盾,到後來我己經對「變得得體」很執迷,久而久之反而發現自己好像過頭了,已經沒有站在任何立場,沒有任何要堅守的東西了,覺得怎樣都可以,當然我認為我一定還是有想要堅守的價值,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主義或是體系可以代表這個價值。
葉|當時的壞脾氣如何被表現出來?
許|容易發怒,講話不好聽,但不是尖酸刻薄,因為尖酸刻薄還有一點幽默感,我以前是完全沒有任何幽默感的。暴躁、亂罵人、想惹麻煩、現在想想好像是想找架打的心情,雖然我不是很強的不良少年,但當時我很想變成不良少年……但其實是很膽小的,一發生衝突我是無力招架,是一直想著逃走的。那是16-24歲的時候,心裡有股怒氣,很想跟人起衝突。學生時期我曾經休學三次,那時候都不回家跑去淡水跟朋友混,那時我媽很擔心,都找不到人,後來不知道哪裡問到我朋友的手機,我朋友知道我媽原來那麼擔心就把我趕走了,其實他也算是還不錯的朋友。
葉|你說過捷運通了以後天母變得很遙遠?它和創作的關係?
許|就是市民的心理距離,當交通不方便的時候去哪都差不多麻煩,一個比較方便的交通手段,像是捷運出現之後沒有捷運的地方就變得很遙遠,就是很不直覺,你就要「特地」去那個地方,而且現在就連騎車都懶得回天母,這地方與市區感覺上是相隔開來的。但畢竟是老家,我國小就從石牌搬到這裏,學習與成長過程,好的壞的都發生在這,這對創作的關係是從基礎上的影響,很全面的,但其實真的要具體的說影響了我什麼也說不太出來,這很幽微。
葉|你喜歡的作者是誰?
許|我小時候很討厭閱讀,連金庸、古龍也沒看過,唯一有印象的讀物是亞森羅蘋,這套書我應該有看完,還不錯;只是基本上還是個無法靜下心來看書、很浮躁的小孩。我小時候喜歡玩電動遊戲、散步、坐公車,這些事比較能帶給我刺激跟思考。說不上喜歡哪個作者,但有幾本書印象滿深刻,《鎮上最美麗的女人》查理布考斯基、《異鄉人》卡繆、《麥田捕手》沙林傑,都是一些大眾讀物,沒什麼好特別介紹的。倒是20歲時看布考斯基會覺得很暢快,很刺激,怎麼會有人這麼壞,什麼都不相信,它不是什麼經典,但是在那個時代是個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