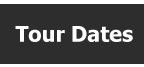|
以下編輯部簡稱編,楊大正為大正
五月天的影響力
編|如果要講台灣搖滾,就不得不提到五月天,五月天對你來說有甚麼樣的意義嗎?
大正|在2000年以前我是一個熱愛華語金曲的人。他第一張專輯的歌我全部超愛,也有買CD,會去一直反覆聆聽的那種。但有趣的是,早期開始玩搖滾樂的時候,那時的氛圍會很反抗主流,所以我也跟著大家一起說五月天太芭樂甚麼的...。
當你在樂器行,所有人都在看國外的音樂錄影帶讚嘆那些吉他riff,大家會說五月天的歌太簡單,都是一樣的和弦……甚麼都可以罵就對了。當然或多或少會被影響,但是五月天可以用時間去證明很多的事情。
經過大概兩三年吧,再去看五月天,可以感覺到他們給自己的使命,透過創作感動很多人,變成如今這樣影響力巨大的樂團。
我在旁邊所看到的,再到後來自己開公司,用不同的思維在面對這個新的時代。五月天有硬體音響公司,有演唱會製作公司,以我們現在這樣在看,五月天本身是個實力雄厚的樂團,可以帶起產業很多不同的面向,這是大家比較不會留意到,可貴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近期音樂產業相關的,比較年輕的技師、音控、燈控等技術人員,都在五月天帶起的這個巨大產業裡,得到很好的經驗累積,這是我對五月天比較讚嘆的地方。
編|所以不只是玩音樂,而是帶動了整個產業?
大正|因為我自己也很看重產業這塊,我常在想,為什麼我後來會開公司、辦活動?就覺得說我們滅火器今天不管是幸運也好或者甚麼的,我們的確是這個產業裡不可忽視的一份子,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運用僅用的影響力,在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做,去耕耘大環境讓他更完整。
我希望未來幾年以後,我們過了可以站在舞台上的年紀,那起碼也留下了一點東西。所以當我意識到這個角色的時候,會發現五月天他們早就想到了然後在做。
編|因為我們在聊的是搖滾樂,所以不只是獨立音樂而是整個台灣的搖滾樂,比如說最近很常聽到的說法是現在有一群年輕人是只聽台灣團的,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大正|有阿,的確有這個族群存在,其實從台灣獨立音樂比較蓬勃開始,應該是2000年附近,台灣有很多的音樂祭、場館、小廠牌,慢慢都有培養出自己的群眾,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正在起頭,自然而然就會有一群人是受這些東西餵養而生的。
餵養獨立音樂創作者與群眾的場景
編|你說你2000年左右開始玩團,可以說說看當時樂器行跟練團室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嗎?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未必和以前一樣,對你來說,樂器行是怎麼樣的場景?
大正|就是舒適圈阿。兩千年左右我還在高中,網路沒有現在那麼好玩,就只有介面很醜的奇摩家族,要不然就批踢踢,所以網路沒甚麼好泡的,也沒有手機可以滑。你如果要找人玩樂,要取暖,要感受一個社群,你只能走出去,所以那裡(樂器行)有你崇拜的前輩,有跟你同時期一起在萌芽的樂手,會有各種碰撞,在樂器行抽煙聊天看錄影帶,看那些買不起的樂器,做做夢。
我覺得就是人跟人的碰撞,你在練團室看別人然後學了一招,或者前輩跟你指點一下: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一個前輩說「你玩龐克那個鼓的session很重要」,就是那種頓拍,會有一點跳躍感。以前真的很土法煉鋼,沒有youtube,也沒有DVD (還只是VCD)。
編|必須要出去實際跟人接觸。
大正|對,每次去樂器行都會有收穫,而且很歡樂因為都是喜歡的人混在一起。
編|是在高雄嗎?
大正|對,真善美樂器。
編|我以前也常去哪裡。

再從台中往南!
編|也聊一下台中的廢人幫?以前網路不那麼盛行的時候,地區之間的音樂會有比較明顯的差距,比如台北可能有英搖跟後搖,台中則是金屬跟龐克之類。
大正|廢人幫的形成是1999/2000年左右,無政府樂團很活躍,以他們為主的靜宜大學;草莓救星雖然不是廢人幫,但也是台中音樂光譜上很重要的一環;再來就是複製人。當時台中有很多很強的樂團,以無政府跟複製人等樂團形成了一個比較金屬跟龐克的場景,甚至是可以跟台北抗衡的。這些人臭味相投,在生命力很旺盛的年紀,就成群結黨組了個廢人幫。當然不是真正的幫派,就是一個很喜歡音樂的年輕人集合,大家混在一起,聽音樂討論音樂,下載音樂彼此分享,可能更像是讀書會的感覺。
廢人幫很厲害的一點是籌辦倉庫搖滾,在那個才剛起步的台灣音樂場景裡面,可以辦現場活動而且票房有三四百張,我覺得很了不起。2001年八月以後就沒有倉庫搖滾,改成廢人party,辦到04年,台中阿拉因為大火燒掉就沒了。
後來廢唱片有發了一張我們的ep,以及一張合輯《廢向陽光廢向你》。
廢人幫是很多人的青春,說真的我們滅火器大概是廢人幫裡唯一還沒解散的樂團,所以你如果要問那些團現在在哪可能也講不出來,但是像Puzzle Man就是複製人的主唱,或者瑪莉咬凱利的鼓手老馬,或者陳櫻桃,我們碰面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在廢人幫一起喝酒,幹了那些白爛事的時光。
編|那個時候你的重心在台中,但後來大港開唱開始,給人一種你跟高雄的連結性很強的感覺,當然那也是你的家鄉,你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台北嗎?
大正|我是08年搬來台北的,那個時候在延畢。我的經濟狀況非常差,大學前幾年都是在做餐飲業;後來我發現餐飲業對我的未來沒有幫助。如果我很喜歡音樂的話,那我要在產業裡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當初的定位就是PA;還有因為我是念電影的,影像後期的聲音製作、前期的錄音師我也做。大二開始到大四這三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學這些,到大四以後我發現我在台北的工作量已經可以負擔我的生活。如果我繼續待在台中,那我唸書的錢,以及往返的交通費成本很高,就想說延畢兩年,直接搬來台北,發第一張專輯,那時候比較衝,也是很關鍵的兩年。
高雄與大港開唱
大正|08年在台北的時候,我們在小白兔發了《我在哪裡》ep,09年發《海上的人》。我的團員們是退伍以後2011年才上來台北的,所以在07年我在思考要回高雄、上台北、還是留在台中把書唸完。但我們在高雄有租一個工作室當基地,用來寫歌編曲,所以也不是完全脫離高雄。
我們跟大港的形象為什麼會綁那麼深,當然因為是The Wall主辦的。我們剛開始發片的時候,Orbis的角色是無話可說的。我會覺得任何回憶都是不可抹滅的,像我現在看到小花或KK,他們都是在我們最沒有資源的時候,團結起來幫助我們,傳承很多東西給我們,這種尊敬的關係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我們是The Wall有料音樂做的,所以可以運用一些主辦方的優勢去做渲染,早期大港開唱我就拍了兩次主視覺海報,所以大家看到呈現出來的是這樣。
我的想法是,高雄有得天獨厚的天氣、城市氛圍,而我是在地人當然也很愛這個城市。但以前幾乎沒有人會討論高雄的音樂人,即使濁水溪公社的主唱小柯是高雄人。2006年第一次大港,當我們那些高雄團發現高雄有了一個有規模的音樂祭,慢慢越來越多人認識高雄的好的時候,會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那些很感動很激動很開心很驕傲的情緒,都是真實的。
編|你剛才說高雄樂團的臉孔越來越鮮明,其中大港在做的絕對是讓這個場景變清晰的關鍵之一?
大正|對啊,那個輪廓越來越鮮明。

終於也把自己搞成產業裡的一環
編|去年你主辦的火球祭、把龐克明星隊都邀過來的感覺是?現在回頭來看,也是希望能夠在高雄把音樂場景、討論帶起來嗎?
大正|我開公司之後有一些想法是比較有趣的,做為一間廠牌,你會發現,這個產業是資方跟勞方利潤都很少的,事實上產業規模就很小。我其實沒有信心這個公司可以開多久,所以我就會問自己還有什麼夢想沒有做完,那趁我現在還有力我就衝一點!
我的音樂祭啟蒙是Hi-STANDARD在2000年辦的AIR jam,他們在幕張棒球場辦了一個全龐克音樂祭。我發現人家的龐克樂可以做到一個棒球場滿場,所以一直有這個夢想!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待龐克,後來市場也證明了這樣的音樂接受度不高,但是我不死心:幹~我從這種音樂得到那麼大的力量跟面對生命的勇氣,還有那麼多快樂,我知道這是好東西!然後我想分享給你們,所以是這種心情。
編|台灣有主流搖滾,但我們所在的搖滾樂,是一些比較邊緣、反動、有一些憤怒,或是比較小眾一點的能量。但大概從2013年開始、到14年甚至是16年,你們在一些典禮上演唱,一轉眼間,台灣的獨立搖滾樂,好像被推到一個很特殊的位置,第一次讓同溫層以外的,不在意這些東西的人知道。現在又過了兩年,你在其中有什麼感觸?
大正|我們的音樂從來不會去計算政治,或是支援政治,完全是以自己為出發點。但是音樂是怎麼跟政治牽連在一起,是人對政治的參與才會發生。我有我的意識形態,有我看待議題的角度,我不會因為我是創作者,就要避掉這些東西。

整個島嶼天光的事情是這樣:
我在2008年321選舉完睡不著,就爬起來彈吉他,寫了〈晚安台灣〉。一氣呵成半小時詞曲寫完,我不是要發行這首歌,只是我的抒發。隔天寄給公司的人聽,然後整個辦公室Freddy、鄭文堂、Orbis聽過都說這首歌太棒了!剛好那時候要發《我在哪裡》就把它放進去,也沒有太多人注意到。但在後來幾年街頭運動,大家超愛播的。在我們共同認同的議題上邀我去唱,我就去唱,但那不是為了我要去抗議而寫的歌。
到了2014年318佔領立院那段時間,一個叫做陳敬元的北藝大學生跟我聯絡。之前在紐約演出時他剛好去參展,我們在那認識。他在訊息裡說,我們計畫要做一個太陽花影像紀錄,在331遊行前,做一隻MV 讓更多人上街頭。他們說可是我們現在沒有歌 ,問我可不可以寫,我問為什麼是我?因為我寫歌很慢。後來他說因為立法院裡面的學生每天晚安曲是晚安台灣,所以大家投票希望我們來寫 。
在那個大家一心想要推倒國民黨的短暫當下,我接到這個有點艱難的任務,如果可以盡一份心力,那我就要做。我到寫完歌是三天完全沒有睡,寫完還包錄,進錄音室錄完,當天我就進立法院拍MV,唯一有睡就是在立法院睡一個鐘頭就拍MV了。拍完隔天,我也沒想什麼;起碼階段任務達成。但是真的恐怖的事情是4月1日,我起床之後電話就被打爆了! 一次有六七間電視媒體要來採訪,我們突然超受注目。
從那之後,我走在路上政治標籤都會貼過來;大家開始對我們的音樂期許就自然而然會把政治因素套在我們頭上。那時候我很慌,跟團員說我們先不要接受任何訪問因為怕講錯話,而且根本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情形。
我們玩了十幾年樂團,每次發片也沒人要鳥我們;突然這樣一個遊行完十幾間媒體要聯訪。我們在網路上寫什麼就變一篇新聞,嚇死誰啊。後來我們聚在一起討論,樂團對我們來說是什麼,做音樂對我們來說是什麼,我們保護好這個本質就好;才可以很平靜地去看待很多事情。
我覺得生而為人,你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都很正常,而且也應該具備。如果你對這個世界還有熱情的話,政治只是過程,那你冷漠避而不談那你相對就是消極的。所以我覺得既然生為一個人,在我的認知是要有所政治參與,這對我來說是一份責任。既然是這樣,我不會去限制他出現在我的音樂裡,因為我是音樂人。
對我來說,我覺得比較不搖滾的是,你有意識型態,然後你自我審查。我很誠實地講,我覺得這跟搖滾是沒有衝突的;但是我從來不覺得我們這個團被看待地這麼政治,是很搖滾的。我會說,你們夠了沒?真的!
題外話.....
編|你覺得為什麼Gibson吉他會破產?
大正|我覺得吉他是一種很不容易壞的東西,不像車子哩程到了就壽終正寢,吉他你好好彈可以用很久,為什麼沒有賣出新的吉他,也許是吉他手或者有收集的人買到放不下了,而新投入吉他市場的人沒有那麼多。
編|那你會覺得搖滾樂out(過時)了嗎?
大正|搖滾樂out了嗎?我覺得搖滾樂不會die啦,但是這種in/out就很難說,你看這幾年也是在流行黑膠跟錄音帶,就只是in in out out而已。
編|現在火氣音樂有哪些音樂人?
大正|火氣音樂現在藝人的話就滅火器,鄭宇辰的新團Empty Orio我比較把它看成是side project,再來就是鄭宜農。
.jpg)
|